TCR-T细胞疗法:开发方法、临床前评估以及对监管挑战的展望
TCR-T细胞疗法在癌症治疗的过继免疫疗法中代表着有前景的进展。尽管其具有潜力,但TCR-T细胞的开发和临床前测试面临重大挑战。这里介绍了临床前测试关键阶段的结构化概述,包括计算模拟、体外和体内方法,并在此背景下介绍了新型疗法的顺序开发过程。旨在系统地概述每个阶段评估TCR-T细胞的过程:从用于预测靶抗原、评估交叉反应性和最小化脱靶效应的计算模拟方法,到设计用于测量细胞功能、细胞毒性和激活的体外实验。此外,这里还讨论了动物模型体内测试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准确反映人类肿瘤微环境和免疫反应方面。所进行的分析强调了这些临床前阶段在TCR-T细胞疗法安全有效开发中的重要性。虽然当前模型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指出了关键差距,特别是在体内分布和毒性评估方面,并提出了需要加强标准化和发展更具代表性的模型。这种结构化方法旨在提高TCR-T细胞疗法向临床应用推进时的可预测性和安全性。
目前,创新的个性化免疫疗法正在经历显著的发展。其中一种方法是过继性T细胞疗法,该疗法通过向患者输注经过工程改造的T细胞,在某些癌症的治疗中取得了突破。这种疗法包括对原代人体T细胞进行基因修饰,使其表达肿瘤特异性受体,包括TCR或CAR。这些修饰使T细胞能够识别并摧毁恶性细胞。由于具有几个关键优势,TCR-T细胞被认为是对实体瘤治疗更有前景的方法。TCR-T细胞对肿瘤细胞中的抗原水平比CAR-T细胞更敏感,并且能够识别不仅表面抗原,还包括胞内抗原,这使它们适用于更广泛的肿瘤类型。此外,TCR-T细胞在实体瘤复杂的微环境中可能表现出更高的疗效,因为它们可以与MHC呈递的抗原相互作用,促进更深的肿瘤浸润并在肿瘤组织内增强活性。另外,与CAR-T疗法相比,TCR-T细胞疗法可能具有较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例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TCR-T细胞疗法的主要限制是需要通过MHC分子识别抗原。因此,TCR-T细胞疗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患者的特定HLA谱型,这要求根据HLA兼容性进行个体化的细胞修饰。这给TCR-T细胞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挑战,而不像CAR-T细胞,后者正在开发标准化的"现货"选项。然而,最近的努力已经开始开发能够与多种HLA等位基因相互作用的多能TCR-T细胞。
肿瘤也可以通过下调或丢失HLA表达而对TCR-T细胞疗法产生耐药性,这会损害抗原呈递,使肿瘤对TCR-T细胞变得不可见。这种现象增加了复发的风险并降低了治疗效果。此外,TCR-T细胞成功识别抗原需要在肿瘤细胞表面与HLA结合的适当抗原处理和呈递。如果这一处理机制被破坏,治疗的效果可能会显著降低。
在T细胞药物产品进入临床试验和获得上市许可之前,必须进行临床前试验。这些临床前试验的目标是评估新药的药理学、动力学和毒理学特性,以预测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与制药不同,目前没有标准化的方法来测试T细胞疗法,虽然2024年8月TCR-T细胞疗法的第一款药物已上市(TECELRA)。因此,临床前研究的规划必须考虑在类似细胞产品的临床试验中发现的潜在风险。
过去与TCR-T细胞疗法相关的安全性问题,特别是那些与意外的"on-target, off-tumor毒性"相关的问题,在临床试验中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和死亡。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TCR-T细胞不仅会攻击表达目标抗原的肿瘤细胞,还会攻击表达相同抗原的健康组织,即使这些抗原的表达量极低。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靶向MAGE-A3抗原(黑色素瘤相关抗原)的TCR-T细胞。在临床试验中,患者出现了心脏毒性,导致致命后果。这种毒性的原因是TCR-T细胞与心肌中表达的蛋白titin发生交叉反应。
另一个意外毒性的例子涉及靶向MART-1抗原的TCR-T细胞,MART-1抗原是一种黑色素瘤抗原。在一些临床试验中,患者对黑色素细胞产生了自身免疫反应,导致白癜风和其他皮肤相关的不良效应。这些反应是由TCR-T细胞与表达MART-1的正常组织交叉反应引起的。
在另一项临床试验中,接受TCR-T细胞治疗的患者出现了针对CEA的炎症性结肠炎,这需要全身免疫抑制治疗,包括使用大剂量类固醇和抗细胞因子抗体。
这些例子强调了在启动临床试验之前进行更严格的临床前测试和彻底评估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潜在交叉反应性的重要性。
为了便于临床前试验的规划,这里整理并系统化了可用的T细胞药物研究现有方案的数据。分析包括了适用于过继细胞治疗的当前国际指南中的信息。
这里旨在为TCR-T细胞开发和审批的关键阶段提供一个简明的通用协议,并同时解决该领域现有的挑战和问题。
TCR-T细胞疗法开发和批准的关键阶段
图1展示了一个概括性的流程图,概述了TCR-T细胞的开发及其临床前试验的进行。该流程图考虑了这些疗法的复杂性以及当前可用实验模型的局限性。

图1 TCR-T细胞制造和临床前试验的流程图。可以用各种计算方法进行的阶段标有星号。这些方法通常在"生产技术开发"阶段使用。
这里重点关注TCR-T细胞临床前试验的关键阶段:"生产技术开发"、"效率评估"和"安全性评估",每个阶段都包含多个步骤。虽然这些阶段与药物开发中临床前试验的一般阶段相一致,但由于自体生物工程细胞制品的技术和功能特性,TCR-T细胞疗法提出了独特的挑战。一个主要挑战是由于输入了人类T细胞,选择合适的动物模型变得困难,这相比传统制药要求更广泛地使用计算机模拟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在设计和开发的初始阶段应用,在研究的后期阶段也被用于预测作用机制和潜在副作用。之前的研究已详细描述了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及其优缺点。然而,该工作首次根据技术生产链的阶段对这些测试进行了组织。
生产技术开发
生产技术开发涵盖了所有阶段,从选择相关的抗原(AG)进行TCR设计和相应的基因构建,到评估使用合成的构建体转导选定细胞的效率(图2)。

图2 "生产技术开发"阶段的流程图。
选择合适的肿瘤抗原
抗原选择是开发安全有效的过继细胞疗法的关键因素。TCRs识别MHC分子结合的目标抗原,这是相对于CAR-T细胞的一个关键优势,因为它允许检测表面和胞内抗原。因此,TCR-T细胞疗法可以针对广泛的抗原,尽管存在与这些抗原在细胞表面呈现方式相关的某些限制。首先,具有与TCR-T细胞识别的肽表位相同的抗原也可能在健康人体组织中表达。其次,健康组织中的肽表位可能在结构上与目标肽足够相似,从而被工程改造的TCR-T细胞识别。第三,不同的MHC分子可能在健康细胞上呈现脱靶抗原肽,导致与工程受体发生交叉反应。因此,虽然理想的TCR-T细胞靶标是一个在所有肿瘤细胞中高度表达且特异的MHC-肽复合物,但在实践中找到这样的抗原往往具有挑战性。
当前的临床试验主要集中在两类肿瘤抗原上:肿瘤相关抗原(TAAs)和肿瘤特异性抗原(TSAs)。
肿瘤相关抗原(TAAs)是在多种健康组织中普遍表达的抗原,但在肿瘤中过表达。例子包括HER2和间皮素。TAAs可以进一步分类为分化抗原和癌症生殖抗原。分化抗原由肿瘤及其起源组织共享,例如黑色素瘤中的MART-1。癌症生殖抗原的表达限于免疫豁免器官,如睾丸和胎盘,包括MAGEs和NY-ESO-1等抗原。由于这些器官不表达MHC分子,这些抗原在精子发生过程中不会被呈递,并且在健康组织中不存在。
在CAR-T细胞疗法中,表达在B细胞上的CD19抗原已成为治疗B细胞淋巴瘤和白血病的主要靶点之一。B细胞的耗竭会导致B细胞再生障碍,但这种效应可以通过免疫球蛋白替代疗法来管理。另一个例子是BCMA(B细胞成熟抗原),它表达在成熟的B细胞和浆细胞上。BCMA是CAR-T细胞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靶点。由于BCMA主要表达在浆细胞上,因此针对它不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类似于CD19。
TAA在不同患者中普遍存在,使其成为抗肿瘤治疗的有希望靶点。然而,由于它们在正常组织中也有表达,尽管水平较低,使用针对这些抗原的工程化受体可能导致on-target/off-tumor毒性。此外,针对这些抗原的高亲和力T细胞可能在胸腺的阴性选择过程中被消除,这使得获得高度活跃的TCR变得困难。
肿瘤特异性抗原(TSAs),或新抗原,仅由肿瘤细胞表达,在健康组织中不存在。例如,突变衍生的抗原代表从特定点突变产生的独特抗原,并且仅在肿瘤组织中表达。这样的"共享新抗原",如KRAS G12D新抗原或PIK3CA,在具有相同HLA等位基因的不同患者中可能是常见的。针对这些共享新抗原的TCR-T细胞目前正在临床试验中。病毒衍生的新抗原,如E6和E7,在HPV相关的癌症中也有表达。虽然这类抗原的应用仅限于某些类型的癌症,但病毒抗原表现出肿瘤特异性,并且对正常组织无毒。此外,单一病毒抗原只能用于治疗具有特定病毒诱导癌症和HLA类型的患者。其他TSAs是从非同义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外的基因组来源的高度特异性肿瘤抗原,例如移码突变衍生的抗原、剪接变异、基因融合、内源性逆转录元件等(例如,肾细胞癌中的HERV-E)。这些抗原在多种肿瘤类型中相当常见。
然而,基于新抗原的治疗存在几个局限性。高亲和力的TSA特异性T细胞在胸腺的阴性选择过程中不会被消除,可以从患者的肿瘤中或健康供者的外周血中分离出来。然而,肿瘤中的新抗原数量相对有限,并且在不同患者之间可能有所不同,这使得为每个个体确定合适的靶标变得困难,并可能降低TCR-T细胞治疗的效果。在使用TSA构建TCR-T细胞时的另一个关键限制是交叉反应的风险。为了防止这种类型的毒性,需要进行计算机模拟研究以排除TCR与非肿瘤性表位之间的交叉反应,包括筛选潜在的氨基酸和单核苷酸替换。
克服针对新抗原的挑战的关键方法之一是开发针对特定患者肿瘤细胞中独有的抗原的TCRs。目前,研究团队正在开发个性化的TCR,以考虑患者肿瘤中的特定突变,从而增加成功消除肿瘤而不损害正常组织的可能性。
准确预测目标抗原对于开发基于TCR免疫疗法至关重要。如今,除了根据文献和临床数据选择合适的抗原外,研究人员还可以利用各种基于计算机的方法。这些工具有助于识别潜在的抗原或表位,这些抗原或表位可能是TCR的有效靶点。这一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MHC呈递抗原的能力、其与MHC分子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抗原预测工具使用算法分析抗原的分子特征及其与MHC分子的关联。这使得可以识别出能够在细胞表面有效呈现并结合TCRs的抗原。同时,识别出对肿瘤细胞具有高特异性的抗原对于减少不良事件和最大化免疫疗法的效果至关重要。
总之,成功进行TCRs治疗应用的关键因素包括靶抗原的选择、靶组织细胞呈递抗原的效率、肿瘤细胞与健康细胞中抗原表达的相对水平,以及适当的HLA等位基因限制。
设计TCRs
TCRs在生物技术中的设计严重依赖于各种序列预测算法,这些算法在生物医学工程产品开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算法有助于识别能够识别特定抗原或表位的潜在TCR,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在TCR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广泛采用各种方法来鉴定能够识别肿瘤抗原的特异性受体。这一过程的主要方法包括:将癌症患者的PBMC或TIL与肿瘤抗原共培养,使用MHC多聚体与T细胞共培养以选择与靶抗原相互作用的T细胞,用人类肿瘤抗原免疫小鼠以分离出能对人类肿瘤反应的高亲和力T细胞,以及通过将T细胞与肿瘤细胞融合创建杂交瘤来生成表达特异性受体的稳定T细胞系。此外,还将健康供者的PBMC与肿瘤抗原共培养以鉴定能够识别肿瘤的TCR。这些方法每一种都在识别可用于癌症免疫治疗的特定TCR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技术的进步改善了识别和选择TCR的过程,提高了其精确性和有效性。
蛋白质结晶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原子位置、键长、二面角等结构数据,包括TCR的数据。这些关于TCRs、MHC-肽复合物和抗原的结构信息有助于设计具有改进结合性和特异性的TCRs,通常利用分子建模和分子动力学等方法。分子建模技术,包括分子对接,可以预测TCRs与MHC-肽复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预测TCR对目标抗原的结合亲和力和特异性成为可能,并能够模拟MHC-抗原复合物的结构。
采用多种方法预测工程化TCRs和抗原的免疫原性,有助于预测可能的免疫反应并评估治疗的安全性。计算机建模还用于预测TCR-T细胞治疗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特征,优化剂量方案和治疗策略。基于计算机的工具可以识别工程化TCRs的潜在外部靶点,从而减少不良反应。机器学习和预测建模进一步应用于预见和减轻与TCR-T治疗相关的潜在不良事件。此外,各种模型通过预测哪些患者最有可能对治疗产生积极反应来帮助患者选择和个性化TCR-T治疗。
几种组学技术用于获取TCR序列。其中一种方法是谱系测序(AIRR-seq),用于系统分析TCR,从而确定其序列和多样性。单细胞测序技术是另一种正在积极开发的方法,通过DNA和RNA分析提供更精确的免疫细胞中受体分布数据。该技术能够识别形成TCR的具体α和β链,显著提高分析分辨率。
其他现代工具和方法,如RNA测序(例如Nanostring)和分泌蛋白组分析(例如使用Isoplexis的Polyfunctionality分析),也被用于研究TCR及相关过程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的作用。RNA测序提供了对T细胞转录组的深入了解,有助于识别TCR的多样性并研究其表达。这种方法能够更深入地了解T细胞在应对各种刺激和病理条件时的动力学和功能。Nanostring技术是一种创新的方法,用于分析基因转录活性和蛋白质翻译,帮助识别不同T细胞亚群特有的特征和分子标志,并表征它们的功能活动。Polyfunctionality方法,特别是使用Isoplexis,能够分析单个细胞的分泌组,允许同时评估多种T细胞功能,包括其效应功能和细胞因子产生能力。这对于更好地理解T细胞的功能特性及其在免疫治疗中的潜力至关重要。此外,3D RNA测序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可以在组织的细胞结构背景下分析基因表达,使其在研究TCR与周围细胞及其微环境的相互作用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分子遗传技术的进步为研究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提供了对T细胞功能及其在免疫系统和各种病理中作用的更深入和更详细的理解。这些工具正在促进诊断的改进和个性化TCR疗法的开发,从而在免疫治疗和生物医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途径。
TCRs生产
基因构建的设计和合成并不总是在单个机构内完成。设计主要是研发任务,通常由研究部门执行,而构建的合成则经常外包给商业公司。这一过程随后是T细胞转染,这是一种将遗传信息插入T细胞以增强其抗肿瘤潜力的技术。
已经开发了多种技术平台用于原代T细胞的基因修饰,包括非病毒平台,如转座子系统(PiggyBac、Sleeping Beauty)、TALEN、CRISPR-Cas9、电穿孔以及利用聚合物和脂质等化合物的基因递送技术。在临床前和临床环境中,编码TCR的病毒载体的生产仍然是最常用的方法。尽管存在随机基因整合到基因组关键区域的风险,病毒载体相比非病毒转导方法提供了显著更高的基因递送效率。它们能够将遗传物质整合到宿主细胞基因组中,确保长期表达。
病毒载体(如逆转录病毒和慢病毒)将遗传物质整合到T细胞的基因组中以递送TCR基因。鉴于目前使用病毒载体进行转导是基因修饰原代T细胞最流行的方法,因此这里将重点评估这种方法的效率。
评估TCR-T细胞转导效率
TCR-T细胞转导效率是一个关键参数,因为它直接影响能够识别和摧毁肿瘤细胞的基因修饰细胞的数量。高转导效率确保有足够的功能性TCR-T细胞来实现治疗效果。相反,低效率可能导致活性细胞数量不足,降低治疗的整体疗效和临床缓解的可能性。此外,评估转导效率有助于确定技术的表现如何以及在细胞修饰过程中可以进行哪些改进。
基因转导的效率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评估,包括荧光标记标记基因、RT-PCR、监测转基因表达水平,以及分析转基因整合到T细胞基因组的情况。
荧光标记基因是评估TCR-T细胞转导效率的有效工具。这种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追踪和量化成功的转基因插入,并监测细胞中标记的表达。荧光标记涉及将编码荧光蛋白的标记基因插入到经过改造的T细胞中。在成功转导后,这些T细胞可以通过显微镜或流式细胞术来检测荧光的存在和强度。
荧光标记的四聚体MHC-肽复合物的设计使得能够通过流式细胞术直接可视化、定量和表型特征化抗原特异性T细胞。pMHC四聚体是由四个荧光素标记的MHC分子组成的复合物,每个MHC分子都结合到一个特定的肽。由于其四聚体结构,这些复合物可以结合到最多4个MHC单元中的3个,从而增强其与靶标的亲和力。多聚体结合分析用于验证TCR的正确组装和正确构象。例如,研究人员使用一种逆转录病毒载体,该载体编码NY-ESO-1 157-165/ HLA-A*02:01特异性的TCR-α和TCR-β链,并具有增加的亲和力,以及特异性抑制内源性TCR的siRNA构建体。通过评估健康志愿者的CD8+和CD4+ T细胞的逆转录病毒转导效率,结果表明87.6%的CD8+ T细胞和89.0%的CD4+ T细胞为四聚体阳性。
TCR-T细胞转导的效率也可以通过RT-PCR进行评估。这种方法可以量化标记基因的存在和表达水平,这对于监测和改进转导及治疗效果至关重要。RT-PCR依赖于使用荧光团的DNA扩增,能够实时监测PCR产物的数量。在评估TCR-T细胞转导效率时,与TCR基因一起插入的标记基因表达一种荧光蛋白,并在其表达水平在整个扩增过程中进行测量。RT-PCR量化了转导的TCR-T细胞水平和标记基因的表达水平,这对于优化实验条件至关重要。此外,该方法还用于监测标记基因在转导T细胞中的长期稳定性。
效率评估
"效率评估"阶段包括两个关键步骤:体外和体内概念验证,旨在全面验证所研究的T细胞疗法的有效性(图3)。

图3 "有效性评估"阶段的流程图。
体外概念验证
无论其来源,选定的候选TCR序列必须进行测试以确认其特异性和有效性。细胞增殖和细胞毒性实验用于确定测试分子是否影响细胞增殖并能够表现出直接的细胞毒性效应。
TCR-T细胞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摧毁靶肿瘤细胞并诱导其裂解的能力。在体外评估TCR-T细胞抗肿瘤活性的最常见方法是细胞毒性实验,其中T细胞与肿瘤细胞或人细胞系共培养。
有许多基于细胞各种功能特征的检测方法,包括酶活性、细胞膜通透性、粘附性、ATP生成、辅酶生成、核苷酸摄取活性和细胞增殖。为了选择最佳的存活率检测方法,必须仔细考虑细胞类型、培养条件和特定研究目标。量化由修饰T细胞诱导的特异性靶细胞裂解通常采用铬(51Cr)释放实验、使用萤光素酶的生物发光成像(BLI)、基于阻抗的细胞分析和流式细胞术等方法。这些方法通常与测量效应细胞因子和/或脱颗粒标志物定量释放的方法结合使用,这些标志物是T细胞对靶细胞发出的特定信号作出激活反应的指标,它们允许评估修饰T细胞的功能。
Cr释放实验
基于放射性铬标记细胞并定量检测质膜受损靶细胞的51Cr释放实验在50多年前首次被描述,并已成为测量T细胞和NK细胞诱导的细胞毒性的标准方法。在此方法中,靶细胞用51Cr进行标记,并与效应细胞以不同比例孵育。在效应细胞介导的杀伤过程中,靶细胞的质膜完整性丧失,51Cr释放到培养基中。使用γ射线闪烁计数器测量上清液中的放射性,其强度与在特定时间内被破坏的靶细胞数量成正比。在研究人员工作中,利用铬释放实验表明NY-ESO-1 TCR-T细胞能够有效地在体外消除NY-ESO-1阳性的黑色素瘤细胞系。
乳酸脱氢酶(LDH)活性的测定
另一种常见的评估细胞毒性的方法是基于测量受损细胞释放的胞质酶活性。LDH是一种存在于所有细胞中的稳定胞质酶,当细胞膜受损时,它会迅速释放到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其活性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定量。
生物发光成像
生物发光成像(BLI)是另一种广泛用于细胞毒性评估的技术,它测量由受损细胞释放的胞质酶的活性。基于BLI的细胞毒性检测利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来测量目标细胞发出的光信号(光子)。这一信号仅由表达荧光素酶转基因的活细胞产生,因此可以根据BLI信号强度的下降来评估效应细胞的细胞毒性。研究人员使用基于BLI的检测方法证明了针对结直肠癌细胞系MSI + HLA-A2 + HCT116的电穿孔TCR-T细胞的细胞毒性。
阻抗分析
基于阻抗的细胞分析是51Cr和BLI为基础的检测方法的一种替代方案。这种方法使用嵌入微量滴定板每个孔底部的微电极来测量细胞黏附期间电极间电流的阻抗。在没有细胞的情况下,阻抗(电极间电阻的度量)接近0;然而,细胞黏附会根据每种细胞类型的数量、形态、存活率和黏附强度改变阻抗。悬浮细胞或非黏附性细胞通常不会显著影响电导阻抗或引起的变化远小于黏附性细胞。这一原理被用于测量非黏附性效应细胞如T细胞对黏附性靶细胞的细胞裂解。有研究中,E7 TCR T细胞的功能,包括IFN-γ的产生和肿瘤细胞裂解,在体外得到了证实。使用实时阻抗为基础的细胞裂解测定法评估了E7 TCR 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
流式细胞术
与上述方法不同,流式细胞仪分析能够研究和量化异质细胞群体中的细胞毒性,为探究混合群体中不同细胞类型对靶细胞的敏感性提供了独特的优势。流式细胞仪根据细胞大小和颗粒度(分别由前向散射和侧向散射表示)以及荧光标记抗体的特异性染色来区分靶细胞和效应细胞。通常使用荧光DNA嵌入剂如PI或7-AAD来评估细胞死亡,这些试剂优先被死细胞吸收,并在与DNA相互作用时表现出光谱偏移。
凋亡阶段可以通过使用Annexin V染色细胞来识别,Annexin V特异性结合在凋亡过程中表达在细胞表面的磷脂酰丝氨酸。标准方法包括评估经过工程改造的T细胞对用细胞穿透染料染色的细胞系的细胞毒性,例如CFSE,该染料与细胞内游离氨基相互作用,随后进行流式细胞术分析。
因此,流式细胞术能够同时分析目标细胞的消除和效应细胞的表型,以及分离异质性细胞群体。
体内概念验证
TCR-T细胞在动物模型中的应用对于验证其体内可行性、功能性和持久性至关重要。这些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挑战是需要将人体细胞注入动物体内。
在使用经过工程改造的T细胞的实验中,采用了多种小鼠模型,包括人源化小鼠模型、同种异体小鼠模型和HLA I类转基因小鼠。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临床前体内研究使用的是来源于人细胞系的异种移植模型,在注入TCR-T细胞之前,将肿瘤细胞移植到免疫缺陷小鼠身上。
例如,在一项使用对免疫检查点抑制耐药的小鼠肉瘤模型的研究中,研究了TCR-T细胞与基于装载长肽抗原(LPA)的支链淀粉纳米凝胶纳米颗粒疫苗联合使用的临床前疗效。LPA由3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包含3个小鼠CD8+ T细胞表位,包括9 m。CMS5a小鼠纤维肉瘤细胞被皮下植入野生型BALB/c小鼠。DUC18 CD8+ T细胞从小鼠TCR识别新抗原的9 m表位的DUC18转基因小鼠中分离出来,从而产生了能够识别CMS5a肿瘤的TCR-T细胞。含有LPA的疫苗和DUC18 TCR转基因T细胞的联合使用成功摧毁了CMS5a肉瘤,而单独使用T细胞则无效。
使用异种移植小鼠模型研究了靶向E7的TCR改造T细胞在体内杀伤癌细胞的能力。靶向E7的TCR改造T细胞的给药导致NSG小鼠的皮下4050肿瘤完全消退,并抑制了CaSki肿瘤的生长。
尽管异种移植模型具有实用性,但它们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这些模型不能准确复制人类肿瘤微环境中的成分,例如免疫抑制细胞的存在。此外,工程化的TCR与p-HLA复合物相互作用,但MHC分子是人类特异的。这种物种差异意味着使用HLA转基因小鼠进行的实验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到人类免疫反应的复杂性。
鉴于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免疫系统的相似性,灵长类动物被认为是评估工程T细胞毒性的潜在大型动物模型。然而,获得自体工程T细胞的需求带来了挑战,并且灵长类动物中肿瘤的自然发生相对较少。尽管如此,灵长类动物模型能够密切复制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的发展,这两种综合征是在工程T细胞治疗中最常见且可能致命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
狗的自发性癌症在临床表现、组织学特征、分子谱和治疗反应方面与人类癌症有许多相似之处。狗和人的癌症之间的生物学相似性也为在患有自然发生肿瘤的狗中测试基因工程T细胞提供了可能性。然而,由于伦理考虑存在限制,例如需要选择一组具有相关自发性肿瘤的动物,以及将人源生物制品注入狗体内时潜在的过敏性反应风险。尽管如此,仍在进行针对狗的CAR-T和TCR-T细胞疗法的研究,其结果可能作为这些T细胞疗法在人类中潜在应用的模型。相反,人类临床试验的结果也可能有助于兽医肿瘤学中T细胞疗法的发展。
近年来,人类体外模型,特别是类器官和组织型系统的出现,有望将TCR-T细胞的临床前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因为这些模型能够模拟人体生物学,并提供某些类型毒性的个性化预测。例如,有研究人员提出使用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这些细胞可以分化为关键组织的特定类器官,用于毒性研究。另一项研究建议使用源自患者肿瘤组织的类器官作为新型临床前模型。这种方法保留了原发肿瘤的关键生物特征。研究人员证明,与肺癌异种移植模型相比,使用患者来源的类器官培养的成功率提高,同时创建模型的时间和成本显著降低。这些类器官模型还预计将更具个性化,提供更好的体外抗癌治疗效果预测。最近有报道强调了3D肿瘤模型,如宫颈癌细胞系的球体和患者来源的类器官,在评估新治疗方法,特别是针对肿瘤细胞和调节肿瘤微环境的免疫疗法方面的潜力。已有研究成功使用类器官评估了CAR修饰细胞的细胞毒性效应。
总之,过继性T细胞治疗的体内毒性目前只能通过人体临床试验可靠地评估。因此,毒性评估主要涉及确定人体组织中是否含有靶抗原,并进行体外测试以检查TCRs对人肽的交叉反应性。
安全评估
安全性评估包括验证测试的T细胞的生物分布和评估其毒性的阶段。这一过程涉及确定病毒特异性毒性、off-tumor毒性和交叉反应性(图4)。

图4 "安全性评估"阶段的流程图。
体内生物分布
在临床前试验中,通常会在动物模型上同时进行生物分布阶段和前面提到的体内概念验证阶段。
研究表明,在小鼠中,过继转移的T细胞可以定位并杀死表达同源抗原的靶细胞,无论这些细胞的解剖位置如何。例如,有实验中,小鼠接受了靶向gp100的T细胞,gp100是一种由正常黑素细胞和B16黑色素瘤细胞系表达的黑素细胞分化抗原。T细胞无差别地迁移到所有组织。然而,经过改造的T细胞仅在表达gp100的组织中表现出效应功能,表明它们在广泛分布的过程中具有抗原特异性反应。在这个小鼠模型中,肿瘤退缩与皮肤和眼睛的自身免疫相关。
然而,用于评估T细胞生物分布的动物模型存在几个局限性。这些模型无法完全复制人体肿瘤微环境的成分,例如人体免疫抑制细胞的存在。此外,它们不适合预测T细胞向患者全身转移性肿瘤部位的迁移。这些生物分布分析中的挑战仍未解决,需要新的方法来应对。
毒性评估
病毒特异性毒性
基因毒性是过继细胞治疗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为了应对这种毒性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各种测试。由于工程TCR主要通过病毒载体递送,因此由于插入性突变和细胞转化的风险,安全性问题随之产生。临床经验表明,这些风险因细胞类型而异。例如,造血干细胞的转化风险高于T细胞。
在使用基因修饰的造血干细胞时,已观察到由插入突变引起的严重不良事件,但在接受基因工程T细胞治疗的患者长期随访中未观察到此类不良影响。
使用慢病毒和逆转录病毒载体生成TCR-T细胞存在插入性突变的风险。随机的载体整合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遗传毒性效应、细胞增殖和克隆扩增,可能引发多种原发性恶性肿瘤。
经过基因修饰的T细胞因载体插入TET2基因(一个肿瘤抑制基因和造血细胞形成的主调控因子)而导致克隆扩增的情况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记录。插入破坏了该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了一个具有治疗效果且显著的细胞克隆的扩增。研究人员将研究队列扩大到39名患者,基于载体整合位点开发了一种预测CD19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反应的模型。另一种克隆扩增涉及在生产靶向CD22的CAR-T细胞过程中载体插入编码E3泛素-蛋白连接酶CBL的基因。
采用细胞制品也已使用转座子递送方法进行开发。早期临床试验显示,通过Sleeping Beauty系统生产的CAR-T细胞未出现严重毒性。PiggyBac (PB) 系统也被成功用于生成CAR-T细胞,但后来的试验报告了CAR-T细胞淋巴瘤病例。
最近的研究表明,T细胞的基因修饰与CAR-T细胞疗法后可能发生的癌变之间存在潜在联系。目前正在进行讨论的几个可能机制包括CAR-T疗法后发生继发性恶性肿瘤,如淋巴瘤或白血病的原因。一个关键因素是在T细胞修饰过程中发生的遗传改变,例如使用逆转录病毒载体递送CAR。这些改变可能会意外激活致癌基因或失活肿瘤抑制基因,促进癌症的发展。
最近,【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nonrelapse mortality after CAR T cell therapy. Nat Med. 2024.】探讨了CAR-T细胞治疗后的非复发性死亡(NRM),包括罕见的继发恶性肿瘤病例。根据荟萃分析,大约7.8%的NRM病例是由继发恶性肿瘤引起的。这些发现突显了进一步研究和对接受CAR-T治疗后的患者进行长期监测的必要性。
潜在的插入突变可以通过研究TCR-T细胞中使用的载体整合模式来评估。不同的整合位点分析方法被应用于识别整合位点。虽然最初的分析是基于PCR的,但处理整合位点测序数据的生物信息学工具正在不断开发和改进。
基因工程领域通过使用位点特异性基因组修饰,特别是CRISPR-Cas系统在过继细胞治疗中的应用,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可能会发生难以预测的脱靶基因切割。这些脱靶效应包括在非预期位点的插入或删除,这可能导致目标位点与脱靶位点之间甚至不同脱靶位点之间的染色体易位。目前有几种用于评估脱靶切割的全基因组技术正在使用中,包括检测工程细胞中染色体易位的方法。有许多生物信息学工具可用于预测使用CRISPR-Cas或其他核酸酶时的脱靶效应,包括MIT CRISPR Design Tool、E-CRISP、GUIDE-seq、Digenome-seq、CIRCLE-seq、SITE-seq和CAST-seq。
值得注意的是,脱靶位点的数量和效率高度依赖于特定的gRNA。计算方法可能无法预测实验中确定的脱靶位点(导致假阴性),而体外方法可能导致假阳性,降低特异性。
Off-tumor毒性和交叉反应性
理想情况下,经过工程改造的T细胞应选择性地靶向恶性细胞。然而,靶抗原通常在肿瘤组织和健康组织中都有表达,这引发了对on-target/off-tumor部位的毒性的担忧。毒性效应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目标组织的可接近性、分布范围及其重要性。
TCR的交叉反应性在TCR基因治疗中代表一个重大的安全风险。TCR识别由HLA I类和II类分子呈递的肽段。TCR结合涉及互补决定区的环与HLA分子及其呈递肽段上的氨基酸残基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TCR结合包括一个不依赖肽的HLA结合成分和一个肽特异性成分。这两个成分对于实现T细胞活化所需的结合亲和力至关重要。当工程化的TCR识别由用于识别相应配体的HLA等位基因呈递的自身抗原之一时,就会发生交叉反应性,导致off-tumor毒性。如果工程化T细胞针对的抗原在重要正常组织中表达,即使水平非常低,这种情况尤其关键。
交叉反应也可能发生在TCR与呈现多种肽的不同HLA等位基因相互作用时,而TCR对这些肽是不耐受的。在构建TCR-T细胞时,需要考虑患者体内的HLA等位基因。在MHC等位基因不匹配的情况下,设计的TCR可能无法表现出对HLA分子所需的耐受性。
使用未经胸腺阴性选择的TCRs时,自身免疫毒性的风险增加,胸腺阴性选择旨在去除自身反应性T细胞。这包括来自免疫小鼠的TCRs或互补决定区带有突变的人工增强TCRs,这些突变可提高亲和力。尽管有效,这种方法增加了交叉反应性和非特异性肽识别的风险。
两种交叉反应情景都必须在临床前试验中进行评估。经过工程改造的T细胞可以强烈地与TCR供体中不存在的HLA等位基因发生反应,而异体HLA分子是免疫原性最强的抗原之一。治疗性TCR的同种异体反应可以通过广泛的体外筛选使用表达不同HLA等位基因的细胞系以及在治疗前对表达TCR的工程改造T细胞进行患者细胞测试来避免。
此外,off-target/off-tumor毒性可能由与模拟肽的交叉反应性结合引起,模拟肽是一种与靶标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并在正常组织上表达的表位。这种脱靶结合到细胞表面蛋白在临床前动物试验中难以预测。
为了评估这种风险,必须通过改变对应肽中的个别残基并观察哪些变化会导致T细胞活化丧失来确定治疗性TCR的精细特异性特征。
有几种方法可以识别TCR-pMHC相互作用中的关键氨基酸残基。丙氨酸扫描是最常用的方法,涉及系统地将每个肽残基替换为丙氨酸。这可以确定TCR结合pMHC复合物所需的氨基酸组合。然而,丙氨酸扫描并未考虑到氨基酸可能被具有相似理化性质的氨基酸替代的情况。突变位点扫描(X-scanning)使用了肽库,其中每个表位残基依次被所有可能的氨基酸替代,克服了这一限制。高通量方法包括使用合成组合库的位置扫描,其中每个位置固定一个氨基酸,而其余肽段由其他氨基酸的随机组合构成。所得序列可以与人类蛋白组进行比较,以预测潜在的交叉反应表位。
此外,还可以利用TCR-pMHC复合物的X射线晶体学数据进行3D建模和基于结构的分析策略。收集到的大量TCR-pMHC复合物结构数据使得机器学习算法能够预测TCR-pMHC结合和潜在的交叉反应性。
由于缺乏足够的动物模型,在临床前研究中无法有效评估经过工程改造的TCR-T细胞的靶向毒性。这仍然是一个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总结
这里总结了当前指南中对测试基因修饰的TCR-T细胞的要求,并提出了进行临床前试验的流程图。尽管该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某些阶段的基因修饰T细胞临床前测试中仍存在知识空白,因为现有的体内模型无法完全展示这些细胞的生物分布和潜在毒性效应。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经验是必要的。应仔细分析正在进行的研究结果,以改进和标准化与TCR-T细胞临床前试验相关的技术。
Ishihara M, et al. NY-ESO-1-specific redirected T cells with endogenous TCR knockdown mediate tumor response and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J Immunother Cancer. 2022;10(6): e003811.
Golikova, E.A., et al. TCR-T cell therapy: current development approaches, preclinical evaluation, and perspectives on regulatory challenges. J Transl Med. 2024;22(1):897.
Svitek N, et al. Systematic determination of TCR-antigen and peptide-MHC binding kinetics among field variants of a Theileria parva polymorphic CTL epitope. J Immunol. 2022;208(3):549-61.
Storgard R, et al. T-cell malignant neoplasms after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 JAMA Oncol. 2024;10(6):826-8.
Gupta S, et al. HLA3DB: comprehensive annotation of peptide/HLA complexes enables blind structure prediction of T cell epitopes. Nat Commun. 2023;14(1):6349.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精彩评论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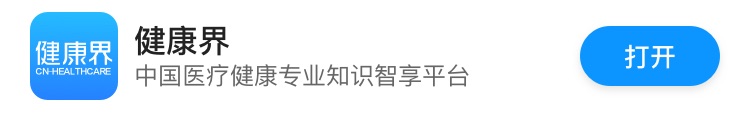




 打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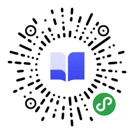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